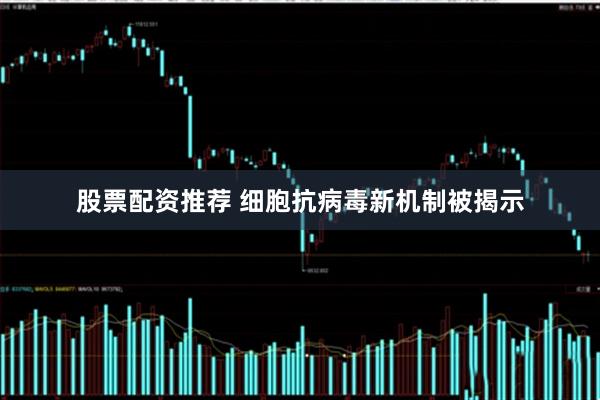[本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人物情节稍作虚构。]
王铁根,
一个在大同煤矿挖了十年煤的汉子,
手上的老茧比树皮还厚。
他这辈子打交道最多的,
是漆黑巷道里的岩石和雷管。
他从没想过,
有一天他要炸的不是石头,
是美国人的铁王八。
当他耗尽心血,
在零下十五度的冻土里埋下的地雷,
被美军坦克像绕开路边石头一样轻松躲过时,
整个连队的希望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肩上。
有人在背后嘀咕,
说炸石头的本事,在战场上不管用。
王铁根没吭声,
只是一个人蹲在战壕里,
盯着坦克压出的辙印,
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
没人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矿工,
脑子里藏着一个能让钢铁巨兽变成废铁的疯狂想法。
这个想法,
源自他在漆黑矿井下摸索了十年的生存法则。

01
1952年开春,朝鲜,云盘山峡谷。
天刚蒙蒙亮,发动机的轰鸣声就爬进了耳朵。
那声音沉闷又霸道,由远及近,
震得战壕里的泥土簌簌往下掉。
志愿军第68军610团三连的阵地上,
战士们的手心里全是汗,
一个个死死攥着手里的家伙。
晨雾像一层脏兮兮的纱布,
勉强能看到几十个黑乎乎的铁疙瘩排着队,
慢吞吞地拱了过来。
那是美军的潘兴式重型坦克,
履带碾过冻土,发出“咯吱咯吱”
的金属摩擦声,听得人牙酸。
每一辆坦克屁股后面,
都跟着黑压压一大片步兵,像蚂蚁一样。
“全体注意,准备战斗!”
连长的吼声在战壕里炸开。
这是美军发动的春季攻势。
自从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美军新上任的司令官就换了打法。
他是个火力不要钱的主儿,
给这次进攻起了个唬人的名字——坦克劈入战。
说白了,
就是拿上百辆坦克当开路先锋,
像一把烧红的刀子,
硬生生往志愿军的防线上捅,
想把阵地切成一盘散沙。
云盘山峡谷是条南北走向的山沟,
中间一条蛇形山道,
是通往志愿军后方的命脉。
要是这里被捅穿了,
整个防线就得被拦腰斩断。
美国人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但他们没想到,
守在这儿的68军,
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专啃硬骨头。
10月13日晚上,
三连指导员把全连骨干召集到猫耳洞里开会。
“同志们,上级下了死命令,
必须组建埋雷小组,
用反坦克地雷把美国人的铁王八给我摁住!”
指导员的语气又沉又重,像块石头,
“谁愿意接这个活儿?”
洞里一片沉默。
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埋地雷听着简单,可坦克长着轮子,是活的。
你把雷埋在这儿,
人家从旁边绕过去,白费力气。
埋在路上?
美国人的工兵也不是吃干饭的,
探雷器一扫,啥都藏不住。
就在这时,
一个三十五六岁的汉子站了起来,
个子不高,皮肤黑得像煤炭,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
“指导员,这活儿我接了。”
说话的正是副排长王铁根,
河北定兴人,1917年生。
指导员抬眼看他:“王铁根,你有把握?”
“我在大同煤矿干了十年爆破。”
王铁根的回答很简单,“炸药,我熟。”
指导员沉默了几秒钟,
煤油灯的火苗在他脸上跳动:
“铁根同志,炸坦克可不是炸石头。
那玩意儿会动,还会开炮。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王铁根点点头,像在说一件平常事,
“给我两个人就行,一个帮我背雷,
一个给咱放哨。”
“好!”
指导员走过去,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就交给你了!注意安全!”
散会后,
班长赵稳重和小组长李小虎立马找到了王铁根。
赵稳重是山东汉子,三十出头,
打起仗来四平八稳,从不冒进。
李小虎才十九岁,河南来的,
性子跟炮仗一样,一点就着,但胆子是真大。
“根哥,我们跟你去!”
赵稳重瓮声瓮气地说。
王铁根打量了一下这两个人,
一个稳,一个冲,正好互补。
“行。明儿晚上就动身。”
当天夜里,
王铁根躺在冰冷的战壕里,
望着天上零星的几颗星星,怎么也睡不着。
他想起了大同的矿井。
1932年,他才十五岁,
就跟着他爹下了井。
那年头的煤矿,人命比驴都贱。
塌方、瓦斯、冒顶,
哪天不死几个人,都算烧了高香。
王铁根在矿上干的是爆破工,
最危险的活儿,也是最讲究技术的活儿。
炸药放多了,巷道一塌,一坑的人都得活埋。
放少了,炸不开岩层,
白费工夫不说,还得挨工头的鞭子。
一个好爆破工,得会听声辨石,
耳朵贴在岩壁上,就能听出里面是死是活。
得会看裂缝算药量,
更得把炸药的脾气摸得透透的。
王铁根在大同井下干了整整十年,
从学徒干到了爆破班长。
他炸过最硬的石英岩,
也放倒过最松软的煤层。
他比谁都懂炸药的威力。
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
王铁根脱下矿工服,穿上了军装。
从矿工到战士,他只用了三个月。
因为懂炸药,他顺理成章成了连里的爆破手。
炸碉堡、毁炮楼、清铁丝网,
别人要来回试好几次的活儿,他一次就成。
但直到今天,他才算遇上了真正的对手。
坦克,装甲再厚,也是铁疙瘩。
只要找准了地方,一样能给它开膛破肚。
明天晚上,就看这第一炮,能不能打响了。
02
10月17日傍晚,天色刚擦黑。
王铁根、赵稳重、李小虎三个人,
一人背着两箱反坦克地雷,
悄无声息地从战壕里爬了出去。
地雷是苏式货,一箱三颗,
一颗就足足五公斤重。
三个人背了六箱,十八颗地雷,
加起来快二百斤了。
他们要去的地方,
是阵地前方两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
那是美军坦克进攻的必经之路,
蛇形山道两侧都是平地,
坦克可以随意机动,路线很难预测。
“都跟紧了,别出声!”王铁根压着嗓子说。
三个人猫着腰,像三只狸猫,
借着夜色的掩护,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摸。
朝鲜的夜,冷得像冰窖。
零下十五度的气温,
呼出的气瞬间就结成了冰碴。
走了一个多钟头,总算摸到了地方。
王铁根趴在地上,
像一头潜伏的豹子,仔细观察着地形。
这是一片缓坡,蛇形山道从中间蜿蜒而过。
路两边有不少炮弹坑,是白天炮击留下的。
坦克要是从这儿过,
十有八九会走大路,或者沿着路边的平地走。
王铁根打开一个木箱,取出一颗地雷。
这是他第一次摸到反坦克地雷。
圆盘状,铁家伙,
直径有三十公分,上面有个压发装置。
只要有足够的分量压上去,
里面的炸药就会被引爆。
“就在这儿埋。”
王铁根指了指山道正中央。
三个人立刻动手。
为了不发出声音,
他们不敢用工兵铲,
只能用刺刀和手一点点地刨。
冻土硬得跟石头一样,
每一下都得使出吃奶的劲儿。
挖了半个多小时,
才勉强挖出一个三十公分深的坑。
李小虎的手指都磨破了,血混着泥土。
王铁根小心翼翼地把地雷放进去,
开始调整压发装置的灵敏度。
这是个精细活儿,也是个要命的活儿。
调得太灵敏,说不定一阵风刮过,
或者一只野兔子跑过,就炸了。
调得太迟钝,坦克压上去可能就是个哑巴。
他闭上眼睛,
手指在冰冷的金属旋钮上轻轻捻动。
脑子里全是当年在矿井下,老师傅教他的话:
“对付死物,就得用活心眼。
你要感觉它,
感觉多大的力道能让它‘开口’。”
他根据经验,
把灵敏度调到一个他认为恰到好处的位置——至少得有十几吨的重量压上来才会响。
美军的潘兴坦克四十多吨,绝对跑不了。
埋好第一颗,又开始埋第二颗、第三颗。
三个人在山道中央和两侧,
一共埋了十八颗地雷。
每一颗的位置都经过王铁根的仔细盘算,
都埋在坦克最可能碾过的辙印上。
埋好后,
又用碎土和杂草仔细伪装,
从远处看,根本发现不了任何痕迹。
忙活了大半夜,十八颗地雷全部就位。
天快亮的时候,
三个人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摸回阵地。
“根哥,咱们就等着听响儿吧!”
李小虎一脸兴奋,冻得通红的脸上满是期待。
王铁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03
10月18日上午十点,
美军的坦克准时出动了。
王铁根带着赵稳重和李小虎,
躲在最前沿的交通沟里,
举着望远镜死死盯着前方。
发动机的轰鸣声再次传来。
十几辆潘兴坦克排成纵队,
像一群傲慢的钢铁巨兽,缓缓向前推进。
但这次,情况有点不一样。
在最前面的那辆坦克前面,
多了一个奇怪的玩意儿——一个巨大的铁滚子,被坦克推着往前走。
“那是什么东西?”李小虎看得发愣。
王铁根的心猛地一沉。
那是扫雷辊!
坦克越来越近了。
500米、400米、300米……
快到他们埋雷的位置了。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轰!”
一声闷响,
走在最前面的扫雷辊压中了第一颗地雷。
一团黑烟腾起,
扫雷辊被炸得跳了一下,
但推着它的坦克毫发无伤,
只是停顿了一下,继续前进。
“轰!”“轰!”“轰!”……
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
但全都是扫雷辊引爆的。
十八颗地雷,就像过年放的鞭炮,
响了个热闹,却连坦克的一块漆都没蹭掉。
十几辆坦克碾过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路面,
大摇大摆地从旁边绕了过去,
继续向后方推进。
李小虎气得一拳砸在土墙上:
“他娘的!美国佬太狡猾了!”
赵稳重也叹了口气:“白忙活一晚上了。”
王铁根没说话,
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些坦克的背影,
腮帮子咬得紧紧的。
他明白了。
美军根本不跟你玩猜谜游戏。
他们知道你会埋雷,
所以直接用最笨也最有效的办法——用一个铁疙瘩在前面开路,把雷全都引爆。
想明白了这一点,
王铁gēn心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走,回去。”
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根哥,咱们就这么算了?”
李小虎不甘心。
“不算了能咋办?”
王铁根的声音有些沙哑,
“雷埋错了,人家有破解的法子。”
回到阵地,三个人一句话没说。
连里有些战士看他们的眼神也变了,
虽然没明说,但那意思很明显:
“还说是什么大同煤矿的爆破专家呢,
结果一辆都没炸着。”
这些风言风语像针一样扎在王铁根心上。
他没去辩解,
一个人坐在战壕的角落里,
从怀里掏出烟叶,卷了一根旱烟,
吧嗒吧嗒地抽着。
烟雾缭绕中,他反复琢磨一个问题——
如果工兵总能把雷排掉,那地雷还有什么用?
有经验的矿工,从不跟石头硬碰硬。
他们会找石头的裂缝,找它的“命门”。
坦克的命门在哪里?
扫雷辊只能扫大路,
那要是把雷埋在它想不到的地方呢?
王铁根的眼睛突然一亮。
对了,不能把雷埋在坦克“可能走”
的地方,要埋在它“必须走”的地方。
哪里是必须走的地方?
它出窝的地方——坦克营地门口!
你总不能在自己家门口也用扫雷辊开路吧?
04
第一次失败后,王铁根把自己关了一整天。
当天下午,他满眼血丝地找到了连长。
“连长,我想再试一次。”
连长看着他憔悴的样子,问:“怎么试?”
“把地雷,埋到美国佬的坦克集结点门口去。”
王铁根一字一句地说。
连长“噌”地一下站了起来:
“胡闹!
那地方叫‘鹰嘴崖’,
离敌人前沿不到一百米,
全是哨兵,你怎么过去?”
“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
王铁根的语气很平静,
“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
咱们敢把雷埋到他家大门口。
那地方是坦克出动的唯一通道,
他们想绕都绕不开。”
连长在洞里来回踱步,
最后停下来,死死盯着王铁根的眼睛:
“你有几成把握?”
“七成。”
“好!”连长一咬牙,
“地雷还是给你六箱。
记住,人比雷重要,不行就撤回来!”
10月18日深夜11点,
还是那三个人,再次出发。
这次,他们的目标更大胆,
也更要命——距离美军“鹰嘴崖坦克集结点”
只有一百米的地方。
那里是一条土路,
从营地里延伸出来,连接到主公路上。
坦克每天都从这条路进进出出,
是唯一的通道。
一百米,在白天,就是一个冲锋的距离。
在晚上,就是一条通往阎王殿的路。
“都跟紧了。”
王铁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从左边的排水沟里摸过去,
那里是探照灯的死角。”
三个人几乎是贴在地上,
用手肘和膝盖一点点往前蹭。
每爬几米,就要停下来,
像壁虎一样趴着不动,听周围的动静。
美军营地里灯火通明,
还能隐约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和音乐声。
探照灯的巨大光柱,
每隔一分钟就从他们头顶上扫过,
每一次都让人心提到嗓子眼。
爬了一个小时,
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才往前挪了不到三百米。
突然,“砰”
的一声,一颗照明弹升上天空,
把整个阵地前沿照得如同白昼!
紧接着,前方响起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声!
“别动!”王铁根低吼一声。
三个人瞬间像石头一样僵在原地。
子弹“嗖嗖”地从他们头顶飞过,
打在不远处的土坡上,溅起一串串尘土。
李小虎的脸都白了,
他感觉自己踩到了什么东西,
一低头,是一根细细的铁丝。
是绊发式照明弹!
王铁根回头瞪了他一眼,用口型做了个
“憋住气”。
枪声持续了足足两分钟才停下。
这是美军的例行骚扰射击,
加上被触发的照明弹,
更是让他们紧张了好一阵。
等了足足十分钟,
确认没有后续动静,三个人才继续往前爬。
李小虎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又爬了半个多小时,总算摸到了那条土路边。
路面宽约五米,被坦克履带压得坑坑洼洼。
路两边是浅沟,坦克根本过不去,
只能老老实实走中间。
王铁根观察了一下,
指了指路面中央的几处辙印:
“就这儿,埋深点。”
赵稳重掏出矿工镐,
李小虎拿出刺刀,开始动手。
这次他们更加小心,
每挖一下都要停下来听动静。
挖出来的土不能乱扔,
要均匀地撒在周围,不能留下一丁点痕迹。
挖了一个多小时,才挖好第一个坑。
王铁根把地雷放进去,
仔细调整好压发装置,
再用土小心翼翼地回填。
填好后,他还用手掌把土压实,
最后抓了把干土撒在上面,
让颜色和周围保持一致。
埋完一颗,又埋第二颗、第三颗。
这次他们玩得更狠,足足埋了十五颗地雷。
整条路面,从头到尾,
每隔两三米就一颗,形成了一个“连环雷阵”
。
美国人的坦克想从这条路出去,
除非长了翅膀,否则必定要中招。
埋完最后一颗雷,王铁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走!”
三个人原路返回。
当他们连滚带爬地回到自己阵地时,
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05
10月19日上午8点,
美军的坦克又准备出动了。
王铁根躲在观察哨里,
眼睛熬得通红,
但精神却高度集中,望远镜死死锁住
“鹰嘴崖”的出口。
他看到,四辆潘兴坦克从营地里鱼贯而出。
领头的坦克耀武扬威地驶上那条土路,
速度不快,但很平稳。
坦克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王铁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轰!”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领头的坦克左侧突然爆起一团巨大的火光和黑烟!
整个四十多吨重的车体猛地向左一歪,
左侧的履带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撕了下来,扭曲着甩到一边。
坦克瞬间瘫在了路中央,动弹不得。
后面的三辆坦克吓得紧急刹车,
慌乱地开始倒车。
王铁根一拳砸在观察口的土墙上,低吼一声:
“中了!”
成功了!
美军营地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几个美国兵想从瘫痪的坦克里爬出来,
被我方阵地上的机枪手挨个点了名。
工兵们跑了出来,
拿着长长的探雷器,
开始在那条路上小心翼翼地搜索。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剩下的地雷。
整个上午,美军都在排雷。
一直忙到下午,
才把剩下的十四颗地雷全部挖了出来。
这一天,美军的坦克进攻计划,彻底泡汤了。
当天晚上,连长把王铁根叫到了指挥部。
“干得漂亮!”
连长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
“一炮就把他们的头车给干掉了!解气!”
“还不够。”
王铁根摇了摇头,脸上的喜悦转瞬即逝,
“美国人已经知道这一招了,
他们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了。”
“那怎么办?”
连长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我再想想。”
回到战壕后,
王铁根一个人坐在那里,陷入了更深的沉思。
这次成功,是靠出其不意。
但这个法子只能用一次。
明天,美军肯定会加强防范。
他们会在坦克出动前,
派工兵把营地门口到主公路的每一寸土地都仔仔细细地扫一遍。
到时候,别说埋地雷,
就是埋根针他们都能给你翻出来。
那怎么办?
怎么才能让美军相信,一条路是“确实安全”
的?
王铁根想了一整夜,
把烟叶都抽光了,也没想出一个万全的法子。
埋在地下的雷,终究会被探雷器发现。
第二天一早,正如王铁根所料,
美军坦克出动前,
几十个工兵拿着探雷器,
像梳头一样把营地门口的土路来来回回扫了三遍,确认没有任何地雷后,坦克才敢开出来。
看着那些耀武扬威的坦克再次从山道上开过,
李小虎气得牙痒痒:
“根哥,这帮孙子学精了!
咱们埋一颗,他们挖一颗,这活儿没法干了!”
赵稳重递过来半个冻得像石头的窝头:
“根哥,吃点吧,人是铁饭是钢,
总能想出辙来的。”
王铁根没有接窝头,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被坦克碾出来的三道辙印。
那辙印在清晨的阳光下,像三条丑陋的疤痕。
他蹲下身,手指摩挲着那冰冷的履带印。
突然,他脑子里“轰”
的一声,像是有道闪电劈过。
他想起十年前在大同煤矿,
一次巷道塌方,一块巨石堵住了出口。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是他师傅,
一个老矿工,
指着石头上的一道不起眼的裂缝说:
“石头不会骗人,它的裂缝就是它的命门。
炸药要塞对地方。”
裂缝……
命门……
王铁根猛地站了起来,
眼睛里爆发出惊人的光亮。
他一把抓起身边的矿工镐,
转身对身后的两人吼道:
“小虎,拿两颗地雷跟我来!
稳重,去通知连长,今晚咱们不埋雷——”
他故意顿了顿,
看着两个战友又惊又疑的眼神,
一字一句地说道:
“咱们给坦克,装个‘铁尾巴’!”
06
“啥?铁尾巴?”
李小虎和赵稳重对视一眼,满脸都是问号。
给坦克装尾巴?
这说的是哪门子话。
“根哥,你没发烧吧?”
李小虎伸手想探探王铁根的额头。
王铁根一把打开他的手,眼睛亮得吓人:
“我清醒得很!跟我来,我做给你们看!”
他带着两人来到后方一个堆放战利品的角落,
那里有一辆前几天被炮火击毁的美军坦克残骸。
“找,给我找一截断了的履带!”
王铁根命令道。
两人虽然不明白,但还是立马动手。
很快,
他们从残骸上撬下来一截大约半米长,
已经扭曲变形的履带钢板。
这玩意儿死沉,得两个人抬。
王铁根又让李小虎取来一颗反坦克地雷和一些工具。
他蹲在地上,开始了他的“发明创造”。
“你们看,”
王铁根指着地雷上的压发装置,
“这玩意儿是靠压力引爆的,对吧?
美国人的探雷器,
探的就是这玩意儿底下的金属。”
两人点头。
“那我们就不让它被压,也不让它被探到!”
王铁根说着,拿起钳子和改锥,
叮叮当当地开始拆解那个压发装置。
他的动作熟练又精准,
就像一个修了十年钟表的老师傅。
几分钟后,
他把原本需要巨大压力才能触发的弹簧和撞针结构,改成了只需要向外拉动就能触发的结构。
他找来一根结实的铁丝,
一头牢牢地绑在改装后的撞针销上,另一头,
则死死地缠绕在那截断裂的坦克履带上。
一个简陋但致命的装置诞生了。
赵稳重看着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
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根哥,你的意思是……”
“没错!”
王铁根拍了拍手上的土,
“咱们把地雷埋在路边的弹坑里,
或者草丛里,让探雷器扫不到。
然后,把这截‘铁尾巴’,
也就是这块破履带,扔到路中间。”
李小虎的眼睛也亮了:
“我懂了!
坦克开过来,
看到路中间有块破履带,根本不会在意。
可它的履带是活动的,
会像传送带一样,
把这块破铁皮给‘吃’进去,
然后带着它往后走!”
“然后呢?”王铁根考他。
“然后……然后连着铁皮的铁丝就会被拉紧,
‘啪’的一下,就把地雷的撞针给拉出来了!”
李小虎激动地一拍大腿,
“地雷在路边,正好炸坦克的侧面!
侧面装甲最薄!
根哥,你这招太绝了!”
王铁根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这笑容里带着矿工特有的质朴和自信:
“这跟咱们在矿井里用绊索放倒矿车一个道理。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咱们不跟它硬碰硬,咱们让它自己弄死自己!”
07
当天深夜,王铁根只带了李小虎两个人。
“稳重你留下,
这个新东西第一次用,人多了反而碍事。”
两人再次摸到了那条该死的蛇形山道。
这次,他们没有靠近“鹰嘴崖”,
而是在距离一公里外的一个拐弯处停了下来。
美军的工兵虽然会排雷,
但他们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营地门口那一段。
这么远的地方,他们只会例行公事地扫一遍。
王铁根选了一个路边的炮弹坑,
把改装好的地雷小心地放进去,用杂草盖好。
然后,他像一个扔垃圾的农夫,
随手把那截连着铁丝的破履带扔到了路中央。
做完这一切,
两人迅速撤回到附近的一个小土坡后面,
只露出两双眼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天边开始发白。
发动机的轰鸣声再次响起。
一辆担任侦察任务的潘兴坦克,
打着头阵开了过来。
它开得很谨慎,速度不快。
当坦克开到那个拐弯处时,
驾驶员显然看到了路中间那块不起眼的破铁皮。
但他丝毫没有在意,
战场上这种破烂玩意儿多了去了。
坦克的履带毫无悬念地压了上去。
“咯噔”一声,
那截破履带被卷进了履带和负重轮之间。
李小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死死地盯着那根绷直的铁丝。
坦克继续往前开了五米、十米……
什么都没发生。
“根哥,是不是……铁丝断了?”
李小虎急得声音都变了。
王铁根没说话,眼睛眯成一条缝。
他在矿下见过太多次这种情况,
引线有长有短,得有耐心。
就在坦克即将转过弯道,
车身侧面完全暴露出来的那一瞬间——
“轰!!!”
一声比之前任何一次爆炸都更沉闷、
更具穿透力的巨响传来!
爆炸点不在车底,而在坦克的左侧腰部!
一团橘红色的火焰从悬挂系统和车体之间喷涌而出,浓烟滚滚。
那辆四十多吨的钢铁巨兽像是被人狠狠踹了一脚,整个车身剧烈地摇晃了一下,然后歪歪扭扭地停了下来,左侧履带冒着黑烟,彻底不动了。
成功了!
李小虎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被王铁根一把按住。
“成了!根哥!你真是神了!”
李小虎压着嗓子,兴奋得满脸通红。
王铁根长出了一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回去!咱们的好戏,才刚开始!”
08
王铁根带着“铁尾巴雷”
的战果回到连里,整个三连都炸了锅。
连长和指导员围着王铁根画的草图,
听着他的讲解,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狂喜。
“好!好啊!王铁根同志!”
连长一拍桌子,
“我马上向团部汇报,给你请功!
这个发明,能救咱们多少战士的命啊!”
之前那些在背后嘀咕的战士,
这会儿全都围了上来,眼神里充满了敬佩。
一个叫小张的战士红着脸挤到王铁根面前,
一个立正敬礼:
“王副排长,之前是我嘴贱,我……我服了!
您教教我们吧,这活儿怎么干?”
“都是为了打美国佬,没什么服不服的。”
王铁根摆摆手,“想学,我就教。”
从那天起,三连的埋雷小组扩大到了整个排。
王铁根成了总教头。
他把自己在矿上学到的所有关于机械、
结构和爆炸的知识,
毫无保留地教给每一个人。
“记住,这玩意儿叫‘铁尾巴’,
也叫‘王铁根雷’!”
指导员在动员会上大声宣布,
“这是咱们工人阶级智慧的结晶!”
战士们开始分头行动,
他们不再去挖坑埋雷,
而是到处搜集美军坦克留下的破履带、
烂钢板。
然后,在王铁根的指导下,一颗颗致命的
“铁尾巴雷”被制造出来。
他们把这些陷阱,像撒豆子一样,
布置在了云盘山峡谷蛇形山道的每一个关键位置。
有的在拐角,有的在上坡,有的在弹坑旁。
每一个布置,
都经过了王铁根的精心计算,
确保能在最要命的位置,
给坦克最致命的一击。
09
10月25日,美军发动了总攻。
他们吸取了教训,
工兵们仔仔细细地把道路扫了一遍又一遍,
探雷器没有发出任何警报。
“道路安全!可以前进!”
美军指挥官得到了报告。
上百辆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
带着震天的轰鸣,再次冲进了云盘山峡谷。
他们以为,清除了地雷,
这条路就是一条坦途。
领头的坦克大摇大摆地前进,
碾过一块不起眼的破铁皮。
它继续前行了十几米。
“轰!”
爆炸在它最脆弱的侧后方响起,
履带应声而断,坦克瘫在路中央。
后面的坦克指挥官咒骂一声,命令绕过去。
第二辆坦克试图从旁边绕行,结果又“吃”
上了一块伪装成石头的钢板。
“轰!”
第二辆坦克也趴窝了。
狭窄的蛇形山道,
瞬间被两辆瘫痪的坦克堵死了大半。
“轰!”“轰!”“轰!”
爆炸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里回荡。
每一声爆炸,
都意味着一辆不可一世的潘兴坦克变成了燃烧的废铁。
美军的坦克兵们彻底崩溃了,
他们不知道这些该死的炸弹是从哪里来的,
它们就像长了眼睛的幽灵,
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
整个坦克纵队彻底瘫痪,
进退两难,
成了我方反坦克炮和火箭筒的活靶子。
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黄昏。
当最后一辆企图逃跑的坦克被炸断履带后,
整个云盘山峡谷安静了下来。
山道上,
十二辆美军坦克冒着黑烟,
像一具具巨大的钢铁尸体,
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美军的“坦克劈入战”,在云盘山下,
被一个中国矿工的智慧,彻底砸得粉碎。
阵地上,
志愿军战士们从战壕里一跃而起,
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王铁根靠在战壕壁上,累得几乎站不住。
他摘下那顶戴了多年的矿工安全帽,
露出一头被汗水浸湿、
夹杂着不少白发的短发。
全连的战士们自发地围了过来,
不知道是谁带头喊了一声:
“根哥威武!”
“根哥威武!!”
喊声响彻云霄。
10
战后,
连长和指导员把王铁根的事迹报了上去。
军部首长亲自来见他,
握着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感慨万千:
“你一个矿工,
比我们这些军事学院毕业的还懂怎么打坦克啊!
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王铁根只是嘿嘿一笑,
露出一口被旱烟熏黄的牙:
“首长,我就是个挖煤的,懂点炸药的脾气。”
后来,这个“铁尾巴雷”
被正式命名为“王铁根雷”,
图纸被下发到各个部队,
在整个朝鲜战场上大放异彩,
成了美军坦克兵的噩梦。
年轻的李小虎在战斗中也成长了起来,
他不再是那个会毛躁踩响照明弹的新兵,
而是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爆破组长。
一次休整时,
王铁根看着李小虎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颗地雷,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虎,记住,煤矿里师傅带徒弟,
战场上老兵带新兵,
都是一个理儿——不管干啥,
都得先想着怎么保住自己的命。
活着出去,才能见着爹妈,才能建设新中国。”
李小虎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眶有些发红。
指导员在战后的总结大会上说:
“同志们,咱们这些人,在家里,
是种地的农民,是挖煤的工人,
是教书的先生。
可只要国家需要,
只要穿上这身军装,
到了这战场上,咱们就是一座山,
一座让敌人永远也啃不动的、
打不垮的中国山!”
11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王铁根被授予一等功。
他没有选择留在部队,
而是回到了他熟悉的那片黄土地。
他没有再下矿井,
凭借着他在战场上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和对爆炸物无人能及的理解,他被聘请为国家级的爆破安全专家,负责培训新一代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为新中国的建设保驾护航。
许多年后,
王铁根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个孙子辈的年轻记者来采访他,
问起了那段烽火岁月。
“王爷爷,
听说您当年一个人就炸了美国人十几辆坦克,
您当时害怕吗?”
王铁根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
眯着眼睛,看着天边的夕阳,沉默了很久。
他从抽屉里拿出两样东西。
一样,是一枚闪闪发光的一等功奖章。
另一样,是一块黑得发亮的煤块。
他把煤块递给记者,缓缓说道:
“孩子,你闻闻。
这东西,有它自己的脾气。
你把它摸透了,它就能给你光明和温暖。
你要是惹毛了它,它也能把天给你掀了。”
他顿了顿,拿起那枚奖章股票配资信息,眼神变得悠远。
垒富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